郑国权:泉州南音原称弦管名正言顺——兼评《海上看中国》援引施舟人“对南音是南洋传来”的论述
(征求修改意见,请批评指正 郑国权初稿)

作者:郑国权▲
福建省泉州市有种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由于它太过于古老,又未见历代的官方和史书对它有过命名或载录,更缺少有人对其历史渊源的研究。因而在民间就有因时因地的随意称呼,至少有南曲、南音、南乐、弦管、南管、郎君乐、御前清曲等等之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接着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这种古乐大有振兴之势,也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发表大批很精辟的论著,也有一些有违历史脱离现实的意见。笔者虽所知有限,但与工作有关,所以很想呼吁为其正名并回复某些有违史实的“意见”。
一种古乐多名并存急待加以正名
上述这种古乐,在民间流行已经很长久,喜爱的人很多,回想抗日胜利后第二年,泉州市区涂山街到泮宫口一带轮到“普度”日,晚间大街中搭了几台戏棚在演戏,而在街的西侧走廊中,有五位男士坐在一起吹拉弹唱,自得其乐。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的场面,后来得知这种场面叫做“(踢投)玩弦管”。
及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泉州市区还有知名的迴风阁、升平奏和俱乐部等三家弦管馆阁在传唱弦管曲目。当年正是弃旧求新之时,为切合时宜,市文化馆把这三家联合起来,组成“泉州南音研究社”。从此,这个乐种之名便慢慢地用“南音”取代旧名弦管。但社会文化生活中,“弦管先生”仍然受人尊敬,“玩弦管”依旧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1956年,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在当年的《人民文学》发表一首长诗,题目则以《南曲》为名,很受爱好文学的年青人念念不忘,黙默记住“洞箫的清音是风在竹叶间悲呜.琵琶的弹奏是孤雁的哀啼在流水上引起的颤栗。而歌者悠长缓慢的歌声,正诉说着无穷的相思与怨恨……”(2000年为泉州地方戏曲研究在出版的《南音名曲选》扉页所转载)。在那时,泉州一些人只知道,蔡其矫诗中所描写的,是老百姓喜爱的音乐,并不在意它还有弦管、南音、南曲等等的名称,也分不清它是南曲或北曲。因为当时的主管部门还没有为之正名的要求。所以从1981、1982、1984年泉州市举办三次这种古乐的国际大会唱,则一律以“南音”为名。
可是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对泉州这种古乐,却以“福建南曲”为条目名,称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又名南音、南乐、南曲、管弦等多名并称,似乎也没有肯定哪项是正名。同是这一年,以中国音协副主席赵沨为首的多位知名音乐家,在泉州成立了一个隶属于中国音协的学会,亦以“中国南音学会”为名。而省里的王耀华、刘春曙两位先生于1989年合作的专著,便以名为《福建南音初探》出版,同样不见有人对其书名有什么异议。及至本世纪初,国家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文化界各部门都热烈响应、大力支持。2002年7月16日,泉州市政府启动南音“申遗”工作,召开专题会议。本人虽已从文化部门退休,但还在民办的地方戏曲研究社工作,所以被通知与几位同事出席会议。会中热烈讨论了本乐种的历史渊源和正本清源的问题,以期申报成功。市长要求大家要为南音多写点文章。会后,笔者自选题目先后写了六篇,头一篇的题目就是《泉州南音应正名为“弦管”》,于2002年8月27日在《泉州晚报海外版》发表。其后五篇引用多位专家的论点,描述泉州南音(弦管)是从汉唐以来“历代积淀、多元形成、幸存泉州、传向四方”的非物质的音乐文化遗产,具有“古、多、广、强、美”的五大优点,应当有望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也先后发表,之后并把这些观点应用在初期的申报文本中。
在这个时机,出版三十年左右的《中国音乐词典》,也启动增订工作。其编辑部发函和修订提网邮到泉州,经辗转多处最后转交给我,我不再推托便接受下来,因为本社多年来抢救出版一批明清戏曲弦管刊本,从中获得不少新的历史信息,也想应该在《中国音乐词典》中有所体现。其中最重要的凭证,是1992年,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1920—2002)辑录出版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集三种》,其书名赫然出现了“弦管”一名,可以用此件明刊古本作证,为南音正名为“弦管”。另一旁证是,在这之前一年的198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任所长、当代研究古乐的著名专家黄翔鹏先生,到泉州参加南音学术座谈以后,回到北京发表了一篇《“弦管”题外谈》的文章(请见“泉州南音网”〈学术园地〉),就堂堂正正以“弦管”为名。他在文中说:“泉州南音它既与历史乐种有着诸种联系,本身又是当代犹存的乐种。”
那么,南音“与历史乐种有着诸种联系”,表现在那些方面呢?笔者以为:南音原名“弦管”的称谓,是这种联系的重要标志。紧紧抓住“弦管”这个标志,我们就可以溯本追源说南音与中国古代音乐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是硕果仅存的遗响!
恰巧的是,1986年,台湾的吕锤宽教授,早于上世纪便依据泉州弦管先生曾省提供的《泉州弦管指谱》为据,加上十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后认为,南管最科学的名称,应该是泉州弦管。于是他编撰的一函三本大书,就以《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为名出版。这当然是增添了有力的铁证。此后,在市文化局向上级的报告文中,也郑重其事申明南音应以弦管为正名,以避免与邻近省市的“南音”重名。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我社出版的十多本曲谱选集,以及协助晋江市编排出版的“指、谱、曲”,都概以“弦管”为名,海内外众弦友无不欣然接受。所以“泉州南音,原称弦管”,便已成为海内外弦友的共识。
基于以上的历史资料和全新的信息,我就把修订的任务接受下来,先后增订和修改了十多个条目,其中主要是针对“福建南曲”这一条,修改为“泉州弦管”。其理由,一是有《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集三种》等作为充分的历史凭证,又有多位音乐史家们对泉州古乐的论述。二是泉州这种古乐只在闽南人中传播,局限于以泉州为主的闽南,并不覆盖福建全省,不宜冠上省名。三是弦管自古以来都是用泉腔方言演唱,自然有其地域声腔属性。所以称“泉州弦管”是坚守本份,名正言顺的。
幸得《词典》编委们都很慎重,又多次要求补充材料,并经过认真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增订版”中,把“福建南曲”修订为“泉州弦管”:
“泉州弦管” 民间传统乐种。又称“南音”“泉州南音”,亦称“南曲”“南乐”“南管”“福建南音”等。1952年泉州弦友组成社团,取名“泉州南音研究社”,始称“弦管”为“南音”。(今按:1952年后来复查是1950年)
为“南音”一名引来《南音是中原古典音乐吗?》的质疑
《中国音乐词典》“增订版”的权威认定,公开发行,但泉州南音因乐名引起的纠结,并没有完全消除。缘起是最近有位从北京来的张维维导演,带个团队到泉州拍摄泉州南音“申遗”及“保护”历程的人与事,还特地网购了一本《海上看中国》的书送给我。书是福州大学苏文菁教授主编的,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网购到的这一本,是2021年第4次印刷的,可见是畅销书。张导演可能已先关注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提醒我,要我先看书中的第六章《南音是中原古典音乐吗?》我一看,不禁为之一惊,因为泉州南音原称弦管,从来没人怀疑它的古老性和独特性。何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于2009年9月30日公布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举世公认,事在理在,容不得怀疑。偏偏在五年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海上看中国》,客观上好似对“人类非遗”南音的来源提出质疑,这事非同小可,岂可等闲视之。

在此,我们还得先认真阅读《海上看中国》第六章。这章分四小节。一、二、三节,似乎与“南音”关系不是太大。只有第四小节特別醒目,名为“南音中的古代波斯文化因素”。
对此,我们要说,泉州南音原称弦管,自古以以来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用地道的弦管古谱和闽南泉腔方言古语构成的,哪里有在地球的另一边的“古代波斯文化因素”?这是泉州文化界闻所未闻,以至国内外学术界从来没人提及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
看来《海上看中国》的编著者所说的南音中有“波斯文化因素”,似乎还是言之有据的。是特地引用欧洲汉学家施舟人《对南音的几点研究意见》而来的。施教授“意见”中,不但强调“波斯文化因素”,同样提出质疑“南音是中原古乐吗”,而后肯定“南音是从南洋来的”。
这样一来,泉州南音,原称弦管,不但有“古代波斯文化因素”,而且“是从南洋来的”。
这两个“意见”,关心泉州文化的人士乍一听,都会大感惊奇,一时颠覆了人们固有的认知,无不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反常的说法,与国家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的载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定公布的结论,大相径庭。因此,务必严粛对待,溯本追源,以正视听,否则便会形成名不正言不顺的窘境,有损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会影响对它的保护与传承。
《海上看中国》与援引施舟人教授的“意见”
面对《海上看中国》引用施舟人教授提出的“古代波斯文化因素”“南音是从南洋来的”等等意见,人们一定会先问,这位教授是何方人氏,与泉州传统音乐又有什么关系?
为此,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这位汉学家施舟人教授。
施舟人教授(1934—2021),生于瑞典,祖籍荷兰,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又被称为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他通晓八种语言。1979年起多次来到中国,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他受聘为福州大学建立了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捐献了一万多册图书,创办西观图书楼。施舟人教授曾来过泉州,笔者还与他有过一面之交。时至2004年10月,当时福建省有关领导对他很敬重,准备为他庆贺七秩大寿,但他谢绝了,只有一个要求,想到泉州听南音。为此,省里特地于28日下午派专车送他到泉州来,同时通知泉州市接待。市文化部门安排在孔庙紧邻的蔡清祠南音社,特地组织一场演唱会供他欣赏,待他欣赏了南音多首名曲心满意足之后,笔者提了一套刚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送给他,对他说:这本明刊本,是据龙彼得教授辑录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经翻译其长篇论文和点校刊本以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今年刚出版的。他欣然接下这套书后说:可惜龙先生过世了(1920—2002),不然看到这本翻译校订的书,一定会很高兴的。缘于他与龙先生同是荷兰人,又同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各有侧重。龙先生研究的是传统戏曲与弦管;他研究的则是中国道教,甚至当过道士。但他也喜欢南音。在台湾,他曾经推动台南南声社组团到法国去演唱,首场从晚上唱到黎明,在欧洲轰动一时。因此弦管界对他印象良好,想他有这个热心与经历,应当对南音的现状尤其是历史渊源会有深刻的理解。但今天我看到《海上看中国》书中,引用施舟人教授“对南音的几点研究意见”后,随即触使我回想到,早在十多年前,北京有位大学老师曾经打电话给我,说有位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在北京最近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对福建南音许多与众不同的意见,感到很异常,问我知道与否,我回复不知道,希望能看到讲话稿。转眼过了多年,幸得《海上看中国》的出版,引用了施舟人教授的意见,让我们方便获知他的种种观点。从而感到施教授在该书中的论述或与在北京的论点应该是一致的,由此得知他是一直坚持由来已久的“意见”。
为此,我们也得针对这种“意见”,说说我们的意见。
南音不姓“南”,原称弦管,绝对不是从南洋来的
《海上看中国》的著作者首先在书中说:“南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直被认为是保留了中国古代中原特色的古乐。其实南音在它的艺术层面上与中国其他的音乐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命名、乐器,还是南音表演形式都存在一些差异。为此,我们需要援引海外汉学家施舟人先生对南音的几点研究意见。”
看来,《海上看中国》的著作者,首先概述“南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留了中国古代中原特色的古乐。”然后在“其实”之下做文章,找出南音与称为“古乐”的“差异”,进而提出“南音是中原古典音乐吗?”的疑问,紧接着便作了回答:“南音中的古代波斯文化因素”。随后又发问:“为什么产生在泉州的这个音乐形式被命名为南音呢?”于是再援引“施舟人教授对此提出了四个观点”:
第一,在中国的各种音乐形式的命名上,有着将其同诞生地联系起来的习惯,如湖南梆子、潮州戏、江南丝竹等,都遵循了这一规律。但是,南音作为泉州或者是说闽南地区出现的音乐,又叫南管或弦管,其命名跟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名没有任何关系。据此,施舟人的第一个观点认为,“或许对于福建人来说,南音不是福建本地的音乐,而是从南洋来的。”
对以上的论述,不客气地说,是相当离谱的,是对泉州的历史文化以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大误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因为“南音”之名,并非是泉州原始的,尽管周代就有“南音”之名,只是泛指南方音乐而已。至于当今的南音,原称却是“弦管”,是1950年成立“泉州南音研究社”才改称的。但改称之后,社会文化生活中,“玩弦管”仍然是许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人们对名家仍尊称为“弦管先生”。
至于“弦管”之名,更是值得讲究,它最早出现于汉初刘邦宫中,《西京杂记》有“宫中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说明公元前就有弦管。其后晋书《乐志》又有“始皆徒歌,夕被弦管”的载录。唐代李白、杜牧都以“弦管”入诗。这些记录当然远在中原,或可以说与偏在东南沿海的泉州文化无关。但泉州唐代第一位进士欧阳詹(755—800),在泉州市郊东湖饯客之后,所写的《泉州泛东湖饯裴参知南游序》,就留下了“弦管铙拍、出没花柳”之句。可见唐代泉州就有弦管。即使到晚唐五代时,泉州还可以从弦管中找到与后蜀弦管的密切关系。在后蜀主孟昶和他的花蕊夫人热衷音乐之时出版的《花间集》,有多处以“弦管”、“管弦”描写丝竹音乐的活动。而《十国春秋》记载成都十世纪中叶的社会生活是“弦管诵歌,盈于闾巷”。这种大街小巷都是弦友在唱曲或奏乐的繁盛情境,泉州也出现过,所以难怪泉州弦管早就把孟昶尊崇为孟府郎君即“乐神”,年年隆重举行春秋二祭。到了宋代,徽宗(赵佶)被俘后写的一首亡国蒙尘词,也提到弦管:“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树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由此可知,从汉、唐、五代至北宋末,宫廷中一直有弦管笙琶。
以上所引的事例,大量的即欧阳詹之前的,都发生在黄河流域一带,当然与泉州并无直接关联。但历史上由于中原屡次战乱,从晋人开始了多次中原人南迁,加上“语言随人走”和“音乐随人走的”规律使然,便带来了中原语言和音乐来到福建、来到晋江(原名南安江由此改为晋江)流域居住下来的。所以史书记载晚唐大臣、诗人“韩偓(844—923)挈族来归”,是整个家族南迁的。他逝世后,墓葬泉州西郊丰州九日山,至今仍保护完好。其后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为闽王,其侄王延彬(886—930)出生于泉州,成人后任平卢节度使权治泉州,政绩可嘉,还建立“招贤院”“清歌里”,又是“家中歌伎皆北人”。可见“清歌里”及他的家中,都有来自他中原老乡的音乐家,至于唱什么歌曲,虽然惜无记录,但不能没有弦管。及至南宋末,宋太祖的嫡系南外宗正司三百多人迁入泉州生活,后来宋亡家族修谱中有严禁“夜饮妆戏提傀儡”和“亦不得教子孙童仆学歌唱戏舞诸色”等活动,反映了皇族当年在泉州不能没有文化娱乐话动。时序发展到明代,刻书商从专刻儒家作品,逐步转向编刻通俗文化时,也把历代在民间流传的弦管曲目,汇编为《新刊时尚弦管摘要集》等三种行世,其“弦管”的大批具体曲目都呈现在世人面前。
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泉州的弦管是来自中原,是历代积淀、多元形成的,继而由泉州传到厦门,改称为“南乐”,传到漳州叫“南音”,个别的又叫“南管”。传到台湾叫“南管”。例如早年从泉州安溪旅居厦门的林霁秋先生,于民国初年在厦门编成的指谱集,由上海用石版印刷出版,便命名为《泉南指谱重编》,泉南即泉州及其以南的地区。又如上引的台湾吕锤宽先生的《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等,都明明白白比标示为“泉州弦管(南管)”印在书上。怎能说“其命名跟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名没有任何关系。”
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史料,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传统音乐,是来自中原故土,不是域外异邦。中国历史上把音乐活动表述为“弦管”,距今已有二千多年。而现在神州大地,似乎再也找不到弦管的遗迹了。特别是全国前些年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后,由国务院公布的一、二批国家级名录有一千多名,竟然找不到一个以弦管为名或有间接关系的“民间音乐”品种。只有在第一批榜上的“南音”一项,其背景与实质,就是地地道道的泉州“弦管”!施教授们无视这个历史,更无任何实证,只凭“南音”的“南”字,便认为“南音”是“从南洋来的”,甚至有“古代波斯的文化因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再说同是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龙彼得教授,1964年在欧洲发现上述的《新刊时尚弦管摘要集》等“明刊三种”,经过编辑论述之后于2003年出版的大书,就以《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为名。书中有弦管曲词272首,梨园戏16折,都是用泉腔方言古语写成的,所以龙彼得教授从来不认为它们是“南洋”或“北洋”来的,而标示“闽南”一名,即这种音乐戏曲也由泉州传到漳州和厦门等闽南三地。四百年前刊行的《明刊三种》中有首《一纸相思》是写秦代的故事,曲词中一句“一纸相思写不尽”,要唱九分钟。著名音乐学田青先生在《中国人的音乐》一书中,认为它是中国最慢的音乐。由此可以有力地证明南音在历史上是称为“弦管”的,20年前,施舟人教授曾接下我送给他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就是《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的校订本,《一纸相思》,就是出自这本明刊本。其中四百年前的“闽南”“弦管”两个名词,一个是地名,一个是曲名,都赫然醒目,豈能无视?
如果接受《海上看中国》的视角,按照施舟人教授的“意见”,无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承载丰富的音乐历史文化信息,反而力图割断与中原文化的脉胳,强调说南音是“从南洋来的”,大家一定会说这个人神智错乱,不分南北。因为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音乐的传承,在录音技术和互联网应用之前,都必须有先曲谱(曲词文字和曲谱符号)为载体,同时要有人“口传身授”,缺一不可。所以至迟从清代以来,泉南一带要把南音传到南洋去,都得有弦管先生亲自出马,带着弦管工乂谱,受聘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华侨聚居地和原是福建所辖的台湾传教给华人的学生。总之一句话,南洋的南音绝对是从泉州传过去的,而不会也不是相反从南洋传过来。
试问,如果硬要说“南音”从“南洋”来的,那么人们要问,南音何时从南洋来的,所传的是什么曲谱?又是谁“北上”来口传身授的?证据在哪儿?肯定是回答不了的。何况客观事实是,南洋有许多岛国,又有更多的族群和不同的语言文字和曲谱(如果有的话)和各种声腔,他们如何“北上”,带什么样的曲谱,到北国他乡传授客地固有的古乐?这是基本常识,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反的,南音弦管之所以会传去南洋,是泉南一带的弦管先生,与旅外的乡亲华侨传授南音,缘于他们是同文同种同声腔。否则也无从传起。在南洋这些岛国中以菲律宾的南音传播为最盛行。所以菲律宾把多个弦管馆阁组织成立“菲律宾岷里拉弦管联合会”。华侨吴明辉还拜托弦管先生收集从泉南一带去的曲谱,编印为《南音锦曲选编》和《续编》,编集锦曲一千七百多首,自费在菲律宾印刷,分赠各地弦友。再者是中国的台湾的吕锤宽、林珀姬、王樱芬等多位教授,凡编著的指谱和论文,无不认定这种传统古乐名为“弦管”是出自“泉州”。
“南音中的古代波斯文化因素”根本不存在
施舟人教授认为“南音中的古代波斯文化因素”,是由于“南音代表着一种非常高层次的文化。戏子在中国传统人群分类里属于下九流,是一个很不被人看得起的职业,在这种职业圈中,产生不出创作南音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据此,施舟人教授提出:南音最早是宋元时期来到东方的贸易之都泉州进行贸易的波斯商人从家乡带来的音乐,他们在异国他乡重拣家乡的音乐,聊以慰藉自己的乡愁。
在这一论述中,施舟人教授无视两国的文化和语言文字的不同,误以为中国的方块文字与波斯锲形文字,可以无差别地通用似的。实际上无任何先例,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又认为波斯人“他们在异国他乡重拣家乡的音乐,聊以慰藉自己的乡愁”的情景,也决不可能是“波斯商人”,因为数以千计的南音曲词,全是中文,从来不见有任何一首一句或一个字,是“波斯商人”所写的波斯文。而“波斯商人……在异国他乡重拣家乡的音乐,聊以慰藉自己的乡愁。”泉州也不见有这类的事例或传说。相反的,正是泉南一带华侨到南洋谋生立足之后.无不“从家乡带来的音乐,他们在异国他乡重拣家乡的音乐,聊以慰藉自己的乡愁。”最典型的是泉州东海的丁马成先生,早年到新加坡,经营事业走上轨道之后,他就接任当地湘灵音乐社任社长,用中文自创自编弦管曲目数以百计,还組队到英国去参加各民族音乐比赛,受到很高的评价,荣获了两项奖励。近代晋江有位曾先生旅居加拿大,还带去弦管琵琶,但异国他乡找不到同胞弦友,只好自弹自乐,或通过互联网,欣赏故乡弦友的弹唱。
因此说,施舟人教授的论述中,似乎要把南音弦管割断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进而无根据地拉上“波斯商人从家乡带来的音乐”,看来是永远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施舟人教授对南音的来源的质疑,一是“南音不是福建本地的音乐,而是从南洋来的。”二是“南音唱词”、“音乐”和“瑟拓”乐器,都是“波斯商人从家乡带来的”。
可惜的是,这么重大的历史文化问题,只凭想象,而不提供可以看得见的物证或典籍,是无任何说服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本世纪初,发动全球各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泉州南音作为世代传承的中国正宗的传统文化,由中国政府作为第三批申报的项目之一,于200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成员讨论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向全世界发布消息。
下面不妨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信”对“南音”的描述:
中国已经提名“南音”,希望其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南音是一种音乐表演艺术,是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南部,即闽南地区人民文化的核心,也是海外众多闽南华人的文化核心。这种缓慢、简单、优雅的旋律,是由一些特色乐器演奏出来的,比如称为“洞箫”的笛子,一种称为“琵琶”的横抱演奏的曲颈琴,以及其他更为常见的管乐,弦乐及打击乐。在“南音”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第一部分是纯粹的器乐演奏,第二部分包含歌词,第三部分是由合奏伴奏的歌谣,且用泉州方言演唱,或由边演奏响板的人独唱,或由一组四人轮流演唱。丰富的保留曲目及乐谱保存了古代民乐及诗歌,也影响了戏剧、木偶剧和其他传统表演艺术。“南音”深深地扎根于闽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南音”在春秋两季的典礼上演奏,以表达对音乐之神孟昶的敬仰,也在婚礼、葬礼、节庆时在院子、集市和街头巷尾演奏。对于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闽南人而言,南音是故乡之音。
上述“推荐信”强调了泉州南音是“闽南地区人民文化的核心,”和“海外众多闽南华人的文化核心”,对于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闽南人而言,南音是故乡之音。尤其是“且用泉州方言演唱”一句,表明乐种的国家以至地方的属性,决不允许任何跨界侵权的事发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信”及颁发的证书,都编在“泉州南音网”的“大事记”栏目中,可供参阅。)
如果说,南洋某国有其本土传承的“南音”,伊朗又在波斯年代已有许多音乐因素可以传入中国,他们也可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本国的“非遗”项目。如果未及“申报”,一旦发现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他国提出申报,而且正在审议中,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为什么不提出意见。尤其是每次审批的“人类非遗”都向全世界公布,为什么相关国家及其历史文化界人士,对此不发出异议呢!
说到底,上述种种“意见”只是一家空想之言,不是事实,自然站不住脚。所以转眼15周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三年前《海上看中国》第四次的再版,再现了施舟人教授对南音的意见。笔者妄想,如果把这本《海上看中国》,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开展对“人类非遗”申报单位履行保护公约的第三次复查,或可看看这本书以及关注施舟人教授对南音的意见,再作出结论,以正视听。
末了,还得关注《海上看中国》的作者在本章的最后一段话:
“施舟人的这个观点开启了看南音、看中国文化的另外一扇门。长期以来,中华文化都建构在960多万公里的陆域面积里,并且一直在自己的文化中单细胞繁衍。在以前的知识结构里很难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关系——中国文化不影响别人,外国文化也不影响中国文化。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突破陆地的限制,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其带来的启发要比原来的单一视野要多得多。看待中国的每一处文化,特别是像中国东南沿海这么一个长期以来保持跟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区域,应该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既从黄色的眼镜来看,也从蓝色的眼镜来看,这样才能恢复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多样化的色彩。”
在这段文字中,书的作者肯定“施舟人的这个观点开启了看南音、看中国文化的另外一扇门。”但笔者以为,观察中国文化,尤其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恐怕要先看“门内”的文化,再看“门外”的文化。如果连“门内”的文化最普通的事物都分不清(如本土与外来、传统音乐与传统戏曲等的不同),再用“门外”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强加于“门内”,势必有误。如第六章第一节“《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陈三五娘》”中说,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双双殉情,再拉上“陈三被发配到崖州(今天的海南岛)。最后,五娘自杀,陈三知道后伤心绝望而死。”以此来说“这两个姊妹篇告诉我们,东西方人民,在共享不同区域物产的同时,精神是互通的、文化是共享的。”这种说法太牵强了太离奇了,相信所有泉州人、潮州人以及海外泉潮籍华人都不会认同,一定会斥之“胡编乱说”。看来书的作者似乎为要写一个殉情的“文化主题”“《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出发硬把《陈三五娘》”拉上去“殉情”。可叹的是,这种表述《陈三五娘》的故事是完全错了。四百年前的东亚怎可能与西欧的“精神是互通的、文化是共享的。”尤其是《陈三五娘》不论是小说、戏曲、电影,都是美满团圆的大好结局,哪来的“殉情”?笔者主编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一卷有关陈三五娘的三个本子和《荔镜记荔枝记四种》共七种,都是描写《陈三五娘》的戏文,每种的最终都是成亲大团圆结局的喜剧,完全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悲剧。
总之,中国幅员很大,历史悠久。当今全世界许多人都在看中国。不论是“海上看中国”,还是“陆上看中国”,都各有各的立场各的观点。但要准确地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恐怕要在中国的发祥地或传播地,追溯其历史文化源头即中原大地,而不是“海上”,更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于外国汉学家,当然都有可敬可学之处,但引用其观点,总得能经得起历史与事实的检验,以免偏差,事与愿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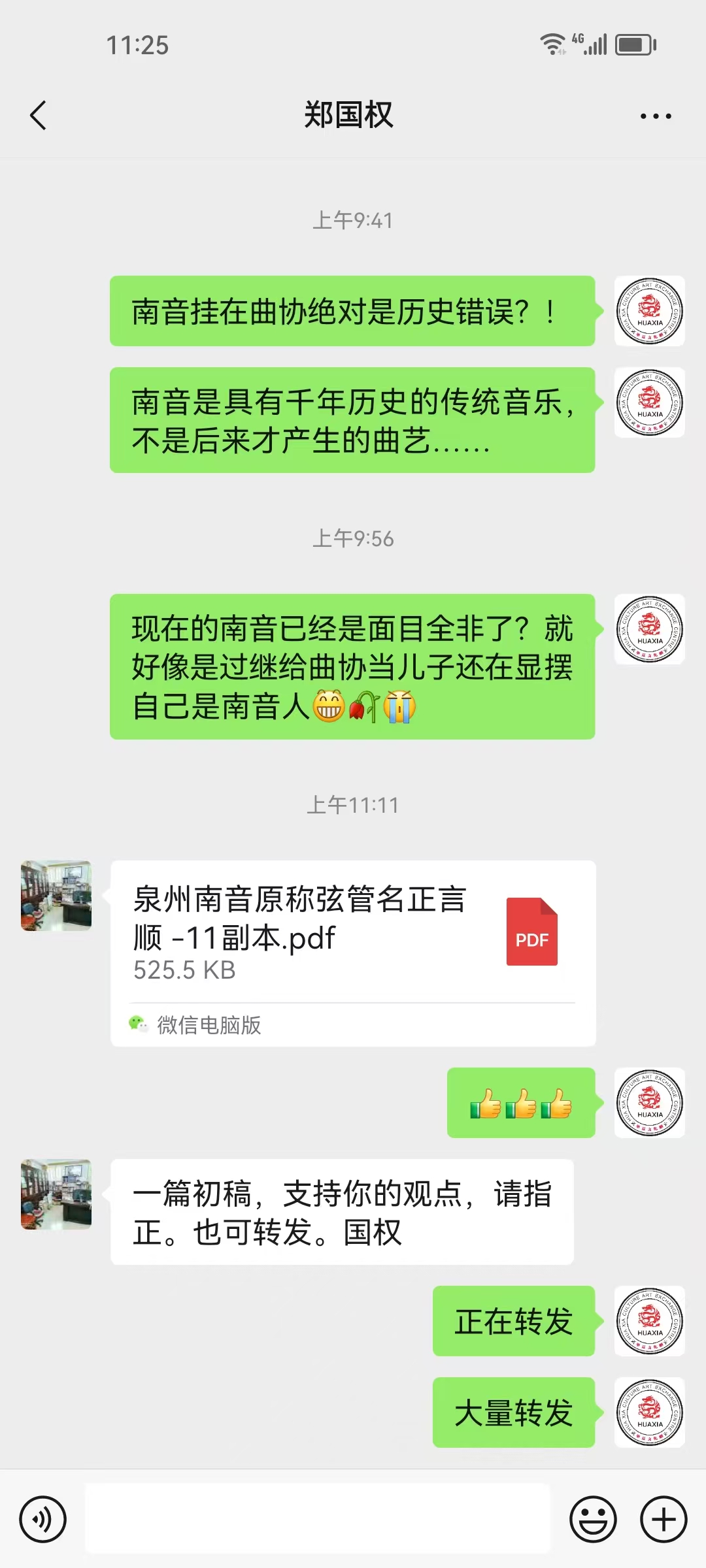
编后语:国际传播时代,如果南音由曲艺形式出国,南音恐怕会有灭种的危机?这个问题可不是小事,也不仅仅是愧对老祖宗的问题了……在国内,如何折腾,都是家里的事,国际上会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哪里呢?

一切所为没有个人利益和目的,更不存在个人恩怨等问题,谨以一名中国文化人的良知为音乐活化石“南音”发声!……
——中国华夏文化网总编辑陈家服